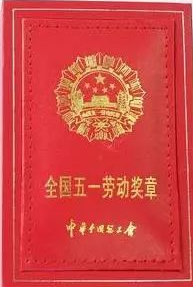母亲
时间:2018-09-02 来源:武汉新市民网 作者:潘和咏 点击: 次
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天了。母亲在世的时候,虽然她在武汉有一处自建的小房子,但她坚持住在乡下老家,一来故土难离,村子里都是熟悉的人事和亲切的味道,她住着舒心。二来她一生独立,不愿意为儿女添一丁点麻烦。因为不放心,我们兄弟姐们每周都要轮流回去看望。现在母亲走了,每个周末我们仍然会不约而同地回去,在老屋母亲的灵前,叫一声“妈”,烧一炷香,添一碗饭,敬献一杯她爱喝的绿茶,陪她坐一坐,说说话。离开的时候,向她作一个揖,对她说:妈,我们走了,过几天再回来看您……
母亲是今年六月突然中风的,倒下去就没有起来。我们在接到村里电话的时候,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晚辈们迅速出发,火速奔回到母亲的病床前,对着不省人事的母亲千呼万唤。她醒来时,已经是三四天之后了,但是已经记忆模糊,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所有亲戚、晚辈子侄和外甥们,纷纷赶来看望,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尽管不认识人,叫不出大家的名字,但是她还是对每个来看望她的人微笑,向他们伸出手,表情还是那么亲切、慈祥,充满爱意和感激。
母亲是一个好性子,一生不与任何人红脸吵架,凡事忍让为先,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计较。她最怕给人添麻烦,却不怕别人给她添麻烦。在我们家几十年,先后悉心照料了三代六个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让每一个老人安详有尊严。她个头瘦小,柔弱少力,却撑着我们家大半个天空。她的无争无求,她的至孝大爱,她的劳苦担当,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以至于在我们的人生中,满是她的痕迹和影子。
母亲年老的时候,一直受到儿女们的尊重和敬爱,也受到村人、亲戚和晚辈的衷心爱戴。在武汉居住的时候,经常有人专程来看望;在老家,更是隔三差五有人问候。村子里不论谁从外面回去,总会给她捎上一点东西:有时是水果,有时是点心,有时甚至是几个馒头。不管是什么,她都很开心,会向我们念叨好多遍。特别是她的那些外甥们,每次来看她,她都笑得合不拢嘴,特别开心,也特别心满意足,逢人便要夸耀一回。
一生习惯于照顾别人的母亲终于病倒了,病得完全不能自理,需要别人服侍照料,这是她晚年最担心的事情;担心在不能动的时候拖累儿女,担心自己死在外面而不是死在老屋。值得欣慰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她的儿女们纷纷表现出至诚至孝的报恩本性,给予了母亲极大的宽慰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姐姐妹妹自不必说,大弟媳妇留在老家服侍,小弟弟毅然辞职回家照顾母亲,还有小弟媳妇,在母亲的病床前撘一个铺,24小时守候。
母亲大小便失禁,弟弟和弟媳妇们不嫌脏臭,不戴口罩和手套为母亲清理,坚持每天给母亲洗两次澡,让母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轻言细语地哄着母亲吃饭、喝水,像逗小孩子一样逗着母亲开心。早上或者黄昏,他们会抱起母亲,让母亲坐在轮椅上,推着轮椅在村子里转一转,在母亲耳边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希望能唤起母亲的记忆。直到母亲病情危重,临去世的那天早上,弟弟还推着母亲在村子里转了一圈,让她与熟悉的村子最后告了一个别……
母亲一生平淡,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生活充满艰辛。她的一生,可以用扁担两头的两桶水来形容:前半生是一桶苦水,她在苦水中浸泡打熬。后半生是一桶清水,她在清水中安闲滋养。与她们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磨练出惊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她在晚年的时候,对于那些苦辛得堪比黄连的故事,总是念念不忘,总是要我们找个能写的人,把她在苦水中挣扎的故事写出来,“比那些电视还要苦”——她坚持这样认为。
母亲名叫汪素娥, 1934年生人,属狗。那个年代,乡民并不知道公历纪年,只知道民国年号,1934年是民国23年,所以母亲一生只记得她是民国23年出生的。十多年前,老家开始登记户口,把她的名字错登为“汪素”,出生时间登记为1936年。户籍登记错了,就不能随意更改,我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为她办理各种证件时,写“汪素”这个名字。小时候我们弄不懂母亲的名字中为什么有一个“素”字。母亲解释说,因为她从出生一直到长大,总是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身子骨又瘦又小。因为太瘦,大人们就给她取了一个小名“素”,因为在乡音中,“素”和“瘦”的读音完全相同。
母亲出生的年代,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战火纷飞,饥馑瘟疫频发,能活下来就是奇迹和造化。她本来出生在黄安(现在的红安)一个叫汪家畈的村落,出生时一个很亲的长辈因为参加红军被杀,整天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两岁时亲生父亲不幸病逝,家庭顿失唯一的依靠,生活陷入绝境,她的母亲无奈只好带着她改嫁到黄陂叶家田一个袁姓人家。好在这户人家对她们娘俩相当不错,并没有把她看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使她的童年虽然贫苦,但享受了家的温暖与爱。逢年过节,汪家畈的几个哥哥,总会轮流来接她回去住几天,享受哥哥和伯爷们的呵护。骑在哥哥们的脖子上,走很远的山路回家,是她童年最幸福的记忆。或许是这样浓浓亲情,给了她一生坚守的善良和慈悲!
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承担了家中很多劳作重任:放牛、喂猪,担水、种菜,砍柴、拾荒,纺纱、织布。还要采摘野菜野果、舂米推磨,日夜不能闲着。冬天时,还要和村中的小伙伴一起到山间田野,去捡拾一种名叫“油籽”的果实,用来卖钱。一个冰天雪地的早晨,她和另外两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一起到一个水塘边捡“油籽”,看到冰面上有一些散落的“油籽”,其他两个小姑娘胆小不敢去捡,我母亲一个人下到冰面上,不料冰面突然裂开,她直接掉进冰水里。四野无人,小孩子又没有气力,她在刺骨的冰水中挣扎了很长时间,才自己慢慢爬上来,没有被淹死,也没有被冻死,真是奇迹。
这大概是她记忆最深刻的“惊险”故事,以至于我们听了几十年。近几年,也许是年岁渐老的缘故,她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捡油籽”的故事。今年四月,我们把她接到武汉住了几天,在接她送她的车上,她反复地给我们讲,给我描述当时的惊险,我们假装从来没有听过,认真听她讲,偶尔插几句话,问一些问题,惹得她精神大好,一遍又一遍地讲,以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车程一个半小时,她重复讲了七八遍。当时我想,母亲变得如此健忘,如此执着地回忆儿时的事,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呢?
母亲刚刚懂事的时候,日本人来啦。乡里人一般把外国人叫做“洋人”,把日本人称呼为“东洋人”,把日本打进来叫做“闹东洋人”。母亲多次经历过“闹东洋人”,尽管那个时候她年龄尚小,许多事已经不记得,但是对亲历的“鬼子进村”,因为惊险,所以记忆深刻,终生不忘,经常向我们提起。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了,村里人扶老携幼“跑东洋人反”,匆匆忙忙到附近的山中树林中躲避。母亲本来跟着人群跑出了村子,但因害怕晒在门前的一件小花衣服丢失,壮着胆子独自回村。刚进村口,就看见村子里到处是“东洋人”,屋顶上架着机关枪,很多“东洋鬼子”在挨家挨户追鸡打狗,弄得鸡飞狗跳。她也不怕,径自回到家门口去收衣服,所幸衣服还在,她拿起衣服就跑,“东洋人”见她是个小孩,也没有把她怎么样,于是她飞快地跑掉了。这是她一生难得的一次“勇敢行动”。每每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总会一脸自豪地说:我也不明白,我怎么那么大胆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微笑。
还有一次“闹东洋人”,一些老人和孩子没有来得及跑出来,被困在村子里。“东洋热”封锁了村子,到处砸门扒墙翻找东西,满村捉鸡子,把村子里的鸡子抓了个干净。有一个老奶奶,坐在织布机前一动不动,任由强盗们肆虐抢劫。等“东洋人”走后,老奶奶才从衣服里淘出藏着的一只老母鸡。村里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一只活生生的鸡子,安安静静地在老奶奶的破棉衣里呆了那么久,不叫不闹,也不瞎扑腾呢?难道鸡子也知道危险就在身边,晓得利害吗?这是母亲一生没有弄明白的事情。
母亲天生胆小,小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家里穷,没有自家的田地,几块菜地也是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山洼子里,经常有野兽出没。母亲最害怕的是一个人去菜地种菜摘菜,但是又不能不去,每次都是提心吊胆,害怕得不行。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一片萧索,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又去菜地摘菜,看见菜地的垄沟里有半条死狗,明显是狼咬死吃掉的。之所以只吃了一半,可能是因为狼看见有人来了,悄悄躲了起来,并且就在附近。吓得她扔掉菜篮子,拔腿就跑回了家,从此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菜地了。
母亲的胆小是比较有名的。2005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她不敢在老屋居住,每天到邻村妹妹家过夜。很多人劝她不要怕,但是她总不能胆壮起来。无奈我们在征求全村人同意之后,在村子中间为她盖了一个小屋,配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嘱咐她每天晚上点灯睡觉。村里人不论是谁,晚上经过她的屋子,总会喊她几声,给她增添一点胆气。后来我们在武汉给她弄了几间房子,她也要开着灯才能睡觉。这种胆小怕事,估计和小时候受到惊吓有很大的关系。
母亲的娘家有两个:一个是红安的汪家畈村,是她的出生地。一个是黄陂的叶家田村,是她的成长地。对这两个地方,她都有着浓厚的感情,没有半点厚薄之分。母亲晚年的时候,娘家的亲人们接她去住一段时间,她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逢人便说以前的人和事,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在娘家人对她极好,给了她极大的宽慰。回娘家一趟,她就会精神大好,红光满面,比吃了蜜还要美滋滋。我们看了,也极为感动。只要娘家人来请,母亲就会欢天喜地地收拾东西,乐颠乐颠地催我们快点送她……
母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贤惠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更没有读过“朱家一本教儿经,万古流传到如今;若是人家有一本,兴家创业人上人”之类的“经典”,却在骨子里,继承了世世代代传统的孝悌之道,体现在无声的一言一行之中。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尊老爱幼,不惹是非。有怨不结,有恩必报,待人以礼,忠人之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歌颂与倡导的一切美德,集于她的一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是一个榜样和标杆,是一本难得的教科书,是一部活的“德行篇”。
母亲后来有了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基本是母亲带大的。大弟弟不幸夭亡,于是对小弟弟更加爱护。从我们记事起,她就要求我们要对舅舅好,不能有一丁点的不恭敬。只要是舅舅来家,她就欢天喜地,高兴得不行,忙前忙后张罗着炒菜煮饭,生怕舅舅没有吃好喝好。在她病重弥留之际,舅舅来看她,她总是伸出干枯的手臂,握住舅舅的手,深情地望着他,露出依依不舍的挚爱之情,令人动容。她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兄弟姐妹,永远不能对舅舅不好。去年舅舅过七十岁生日之前,母亲反复叮嘱我们,一定不能缺席舅舅的寿宴,直到我们纷纷赶回来了,她才放下心来,露出欣慰的笑容。母亲去世后第三天,舅舅和我们一起到坟山为母亲“覆土”,一只美丽的蝴蝶一直围着舅舅飞,落在舅舅的手上,不肯离去。伸手去抓,蝴蝶也不飞不动。我们坚信,这只蝴蝶一定是母亲幻化,轻轻地来与舅舅惜别……
母亲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不仅仅是生育了我们姊妹五个,对待家中的老人真的是无微不至,耐心周到。老人们亡故前都是久病,大都是卧床不起很长时间,母亲一点也不嫌弃。爷爷当年是患直肠癌去世的,患病的时候,严重便秘,总是母亲和我妹妹为爷爷一点一点地抠,再为爷爷洗得干干净净,从来没有怨言。家中的老人,走得都很安详,很有尊严。母亲为我们家族做出了大孝大爱的榜样。母亲自己病了,儿女们如此尽心尽力服侍,恪尽孝道,平和安详而去,后事处理得顺利周到,是母亲一生种下的莫大善因,结出的莫大善果。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之“异熟果报”,在母亲身上,得到很好的诠释和验证。
我家一直是村里村外有名的贫困户,以前叫“缺粮户”。人口多,劳力少,缺粮是常态。我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曾经多次饿得大哭。读高中时,在学校一天只吃两餐,节省的米粮,要卖掉买书读。即便常年吃了上顿愁下顿,母亲也能热情待客,于礼节方面毫不马虎。秋收之后,秋猎开始,远方本家的秋猎队,总会落脚在我家,每次有一二十人不等,在我家打地铺睡觉,在我家灶膛搭伙吃饭,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当然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可以学着猎人们打着绑腿,威风凛凛地随着秋猎队进山打猎,好玩的很。但是可难为了母亲,每天除了要侍候我们一大家子,还要照顾好客人,让客人们满意,着实太不容易了。此外还有那些游方的货郎、要饭的“花子”、阉鸡的本家等等,只要来我们村,都是把我家作为落脚点,母亲对待他们,从来不厌烦、抱怨,总是笑脸相迎,让人家有宾至于归的感觉。那些拾荒的外乡人,四处迁徙的放鸭人、行脚的路人、补伞修鞋和打铜磨刀的师傅,只要母亲看见,她就会同情人家远离乡土,生活不易,想方设法给人家送些时蔬腌菜粥饭之类,接济和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城市青年,高中或者初中毕业以后,大都要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那里大有作为”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国家给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下乡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大部分知青被集体安置在遍布全国的“知青点”,少部分投亲靠友分散于村乡巷闾。我们家也先后接纳了两个知青——三爷爷的两个儿子,爷爷的亲侄儿,父亲的堂弟,我们称呼“叔叔”。他们“下放”到我们家的时候,只有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前后呆了6年。
两个知青叔叔称我母亲为嫂子,而我母亲,则充当了“嫂娘”的角色:既要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包括一日三餐、缝补浆洗,还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舒服开心,安全健康地成长,不能有丁点闪失。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钱缺粮的日子,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母亲每天扯着愁肠算计日子,“借”和“赊”就成为母亲每天的常态:借钱、借米、借油;赊烟、赊盐、赊酒。借了还,还了借;还请赊账,然后再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向前熬着。因为穷,远近的供销社和商店,都不愿意赊账给我们家,有时只好用两三个鸡蛋,到供销社,换三五根烟,打二三两酒,灌半斤煤油,这已经是有面子的时候了。
母亲身材瘦小,又只有一个肩膀能挑担子,不会“换肩”,所以挑东西特别费力。我们生产队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要到相对比较富庶的邻县——红安去借粮,收获后再连本带息送还。这一借一还都是车推肩挑,远路无轻但,辛苦得很。一般男人用车推,女人用担子挑。每次借粮还粮,要挑着重担走几十里山路,母亲总是把年龄尚小的姐姐带上,一来有口集体饭吃,二来姐姐可以和母亲换着挑一挑,不至于掉队。但是一趟担子挑下来,两个弱小的身子,会难受好几天。
就是这样一副柔弱的肩膀,却挑起了全家11口人的生活重担。母亲用她的善良、坚韧和信义,把一大家子人拢在一起,和和睦睦,没有抱怨,没有争吵,没有算计,一个典型的乐呵穷人家。也以她的温顺的性格和高尚的人格,构建了一个和谐宽松的邻里关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母亲用浓浓的真情,深爱着每一个亲戚和晚辈,不论是她娘家的内侄,还是姑妈家的外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她都给予了无尽的牵挂和呵护,视同己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尊重她,爱她。逢年过节,大家都要来拜望她,和她说说亲热的话。她生病了,所有的亲戚,无论老小,都来看望。姑妈家的几个表姐妹和表弟,更是多次来到她的病床前,给她莫大的宽慰。母亲在还能言语的时候,经常非常自豪地说:我的那些内甥、外甥们,哪一个都没有忘记我……
不仅那些亲戚、晚辈没有忘记她,那两个当年下放在我们家六年之久的知青叔叔,也从来不曾忘记他。经常偕同三爷爷家另外的姑姑、叔叔们回来看她,嫂子前嫂子后地叫,透出无限的亲情。每当他们回来,母亲就格外高兴,和叔叔们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吩咐我们招待好叔叔们,生怕他们受到一点怠慢。母亲弥留之际,我给叔叔打电话,告知母亲的病情。叔叔大为惊讶,狠狠地对我说:你再晚告诉我,我会搞你的人的!尽管叔叔说了气话,但我也很感激,这是叔叔们对母亲恩情的一种迸发,是藏于内心深处的一种亲情,日久弥深。
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在离家很远的镇子上,中间隔着宽大的木兰湖,上学放学很不方便,所以只能在学校住读。学校有简易的食堂,为住读的学生提供蒸饭的蒸笼,但不负责热菜。每逢周日,我们返校之前,母亲总是要给我准备好一周的大米和菜。菜是用罐头瓶子装着的,瓶子的下半部装着腌菜,上半部装着青菜。上面的青菜供每周前几天吃,下面的腌菜供后几天吃,因为没有冰箱冷藏,青菜保存不易,只能这样。
为了让我能吃饱饭,母亲总是悄悄多给我舀一些米,反复叮嘱我要吃饱。可是我每次总会把米偷偷卖掉一部分,用卖米的钱买些小说和读物,晚自习后躲在蚊帐里看,看得津津有味。所以我每天只吃两餐稀粥,经常饿得头昏眼花,肚子咕咕叫。好在母亲在我周末回家的时候,想尽办法给我开小灶,让我吃饱吃好。白米饭是难得的奢侈品,母亲也没有办法满足我,只能在我的碗里,尽量捞一些干的,多些米粒,少些红薯,菜里多放几滴油。运气好的时候,弄些乌龟王八在锅里一锅煮,然后关起门来偷偷吃——那个时候乌龟王八多,乡人不吃这些东西,所以吃乌龟王八,是极为丢人现眼的事情。
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令母亲操心的是我。高考后上大学没有钱置办衣物行李,学费没有着落,母亲督促父亲四处告借,愁得在屋里偷偷哭。后来在姑妈、三爷爷和大伯等长辈亲戚的支持下,才勉强上得了学。大学毕业后我应征入伍,离家的前一晚,娘俩在油灯下说了大半夜的话,母亲反复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勤快做事,莫怕吃苦,听领导的话,对人要好,不偷不抢,做个有本事的好人。临行前,我把所有的行李、衣物和余钱都留在了家里,只穿了一身最旧的衣服和一双破凉鞋上路。母亲不舍,硬要塞给我十块钱,说穷家富路。我知道这十块钱是母亲出面向人借的,坚决不要,对母亲说,到了部队上,什么都会发,也会有工资,莫担心。母亲坚持要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几十里路外的车站。我乘坐的汽车开出很远,回头看见母亲和父亲,一动不动地目送着车子远去……
我当兵后进了军校,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每月有59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算是高薪。第一次领工资,除了当月的工资,还补发了两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下子领了二百多元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钱,兴奋得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我把大部分钱汇给了家中的父母,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母亲接到汇款后的幸福和满足。想象着父母拿着这笔钱,自豪地去供销社还赊账,还人家的借款。挺胸抬头地买很多油盐酱醋,还给所有好心借给我们的四邻。想象着母亲可以摘掉被人叫了几十年“苦人”的外号,露出舒展幸福的笑容。那几个晚上, 我一直做这样的梦,在梦中和母亲一起欢笑。
军校毕业了,我被派往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去就是半年。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给家里写信,给父母报个平安。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平安回到家,见到自己的父母。头部受伤的那个晚上,我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想着我还活着,想着母亲在老家的日夜守望,我偷偷地哭了。凯旋之后,我给父亲、长辈们买了很多礼物,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皮背心,希望母亲从此不要再受饥寒,永远有温暖。当我迫不及待地日夜兼程回家,出现在村口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拉着我,哭的格外伤心。
许多年前,隔壁村的老乡亲们因同情我们家穷苦,给母亲起了一个外号,叫“苦人”。那年腊月二十九,临近年关,家中却一贫如洗,没有钱置办年货,半两肉也没有买。隔壁肖家湾一个叫肖显能的长辈,看到我们家这个样子,很是同情,动了怜悯之心,把他们家割的年肉匀了几斤送到我们家。母亲千恩万谢,高兴得不得了,一家人总算能好好过个年了。不料一个债主上门要钱,看到了堂屋里挂着的那块肉,对母亲说道:你们家有钱买肉,没有钱还账,对不起了,用这肉抵债吧。母亲可怜巴巴地央求债主,容过年后还债,肉不要拿走,让我们一家老小过个年。债主不依,提了肉便走。好在村子里很多人出来说情,好说歹说,那人还是把肉割走了一大半。母亲很悲伤,也很无奈,大家就喊她“苦人”。
母亲的确很苦。生产队的时候,母亲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每天黎明时分,起床生火烧水,叫醒上学的孩子,打开鸡笼,准备猪食,张罗柴火,做好出工的农具准备。天刚蒙蒙亮,出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七点多钟,匆匆从田地里赶回家做早饭,而后招呼老人孩子吃饭、刷锅洗碗,喂鸡喂猪,挑水扫地,整理家务。然后出工、做午饭,再出工,再回来做晚饭。家务都料理完了,夜已经很深了,还要坐在灯下缝补衣服,做些零碎活。饭菜是母亲做的,但是吃饭的时候,她却很少上桌,总是全家人都吃完了,她才从厨房出来,吃些剩饭剩菜,吃点稀粥腌菜。
母亲是巧手,有几样拿手活。一是腌菜的水平一流,从不酸缸倒缸,特别是腌洋姜,爽脆鲜嫩,别有风味,每到吃饭的时候,一村的老少都端着饭碗来家分享我家“腌洋姜”的美味。孩子们恶作剧,经常偷偷地跑到我们家的腌菜缸里捞洋姜偷吃,母亲看见了,总是笑眯眯地当做没看见。第二个绝活是手擀面做得好。母亲擀面的时候,我们总喜欢在边上欣赏,一招一式,娴熟而精准,快捷而不凌乱,擀出来的面又薄又均匀,口感极好。有一次我又饿又馋,趁母亲不注意,站在锅边一口气吃了五大碗。还有一绝是煎豆腐:豆腐切得匀称,分量划一,下锅煎炸,火候掌握得极好,两面金黄,色泽诱人。此后几十年,我一直爱吃煎豆腐,但总吃不出母亲做出来的那种味道。
母亲是一个很敏感很重感情的人,她养大的猪,被牵走卖掉时,她会跟着猪呼唤很远。她说狗通人性,所以从来不吃狗肉,美其名曰“狗肉上不了正席”。也不吃鳝鱼,说鳝鱼是善人变的……对别人的施恩,她一定要报答。尽管家中长年累月欠着人家的债,但她从来不失信于人,在她的心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论多么陈年的债务,只要条件许可,她总会主动上门归还。有时实在没有办法还钱,她就会向人家保证:父债子还,我有三个儿子呢!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来很多债务,母亲一一偿还干净,并且反复向人家表达歉意和谢意。等她还完了宿债,一身轻松的时候,才肯随我们一起来武汉居住。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也决不允许我们走歪路。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偷拿了姐姐的一块钱,买了笔、墨水和火柴之类。被发现后,父亲让我跪在祖宗的神龛前,用扁担狠狠揍我,揍得我浑身痛极,鬼哭神嚎。母亲破天荒地不仅不护着我,反而帮着父亲责骂我。后来渐渐长大,才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我走正道。母亲说:自己的是自己的,别人的是别人的。只要不是自己的,一根草都不能拿。这句话,我牢记了一生,奉为做人的至理名言和金科玉律。以至于小朋友们调皮偷黄瓜、花生时,我宁可被小朋友们笑话为“胆小鬼”,也绝不参与其中。
2003年,父亲突然病倒,中风引起偏瘫,生活起居困难,精神状态很差。母亲更是起早贪黑,烧火煮饭,千方百计为父亲调理身子,给予病中的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弟弟妹妹们成了母亲最贴身的帮手,弟弟和妹妹请假在家,帮助母亲照料父亲,把父亲照顾得妥妥贴贴。母亲负责调理饮食;弟弟把父亲抱进抱出,洗脚按摩;妹妹为父亲端茶倒水;姐姐也经常回去为父亲延医送药,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也减轻了母亲很大的负担。2005年大年初一,父亲去世,我的夫人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握着弥留中父亲的手,足足两个多小时。看到儿女、媳妇、女婿们一个比一个孝顺,母亲非常欣慰。
父亲去世后,儿女们各自在武汉忙碌着讨生活,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形单影只,很是孤独。夫人建议我们把母亲接到武汉来住,早晚有个照应,免得两头互相牵挂。但我的房子楼层高,没有电梯,爬上爬下很困难。加上母亲一生只会烧柴火土灶,不敢用煤气,中午我们上班之后,母亲的午饭不好解决。于是我们在弟弟们居住的左近,为母亲弄了一个小屋:两小间房子,一个简易厨房和卫生间,一个小小饭厅,总共六十多个平方。房子虽然极小,非常简陋,不像个样子,但毕竟能让母亲有一个安身之地。母亲也很高兴,又能和自己的儿女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每天晚上大家聚在她的小屋子里,听她讲过去的事情,欢声笑语,温馨又和睦。
有一次,母亲在散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左小腿粉碎性骨折。我们把她送到医院,拍片、正骨、打石膏。骨科主任建议最好手术治疗,因为骨折情况非常严重。大家都守护在身边,妹妹当即给单位打电话,辞去工作,表示要全身心照顾母亲。我夫人二话不说,回家清理了住院的东西,取了钱,一起送母亲到161陆军医院。母亲怕我们花钱,坚决不同意住院,更不愿意手术,我们怎么劝也不行,无奈只好打道回府,在家保守治疗。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在治疗恢复的这一百多天里,妹妹日夜照顾母亲,寸步不离。其他子女孙辈几乎每天前往看望,向老人家请安。
真是天可怜见,三个月后,母亲神奇般好了。原先以为即便好了,也会留下残疾,跛脚是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连给母亲治伤的骨科专家也这么认为。但母亲伤愈能下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点后遗症,真是一个奇迹。母亲在2005年、2007年、2017年先后中过三次风,但都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不治而愈,恢复如初。在母亲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伟大与神奇,也看到了生命的无比顽强。但母亲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她坚信,一定是有菩萨、神灵和祖宗在保佑,是她一生做好事结善缘的好报。她说:好事自有好事在,菩萨是保佑好人的。
这两年,母亲坚决不在武汉住了,坚持要回老家去住。她想回到自己熟悉的村庄,和村里村外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在一起。无奈我们只好送她回去,但保证每周有人回去看她,为她准备好日常用品和生活物资,至少让她不为柴米油盐和零花钱操心。每逢周五,母亲就会给我们打电话,问这个星期是谁回去。一旦知道我们要回去,母亲就会一直巴望,拄着拐棍在村外张望,或者搬一个小凳子,坐在村口痴痴地等。看到我们回来了,车子还没有停稳当,她就颠颠地过来迎接,假装责怪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某某某怎么没有回来呢?然后欢天喜地地把我们迎回家去。我们离开的时候,母亲总是反复叮嘱;到家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每次我们一上天兴洲大桥,就会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到家了!
母亲这次中风,病势来得突然,比以往每次生病都更加严重。我们得知讯息匆匆赶回去的,回去时她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再认出我来。问她我是谁,她说出的人名都不是我,令我心如刀绞。母亲走了,从此我们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顿时失去了依靠。母亲是一棵大树,一直给我们遮阴乘凉。如今大树倒了,但大树的根还在,她撒播的爱、善良和宽容的种子,还深埋在温厚的土壤中,随时都会发出鲜嫩的芽。
愿敬爱的母亲在天堂安好,每夜都来我的睡梦,重温无边的温情!恳求母亲,来世还请允许我再做您的儿子!
2018年9月2日

版权与免责声明:
1、本网凡注明“来源:武汉新市民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武汉新市民网所有,网络媒体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须注明出处,并添加本网站链接。如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上述作品,则须武汉新市民网授权。传统媒体以各种方式利用上述作品的须经本网授权并在授权范围内使用。
2、本网凡注明“来源:×××(非本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且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
3、如因作品内容、版权等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作品于本网发表之日起十五日内联系,否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大家都爱看
今日热点
新新闻
网络链接
如果您的网站PR≥4 欢迎申请链接 更多>>
本网特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为常年法律顾问
邮箱:932449293@qq.com whxsmw@126.com 联系电话:18827381718 027-8816 6299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如果您认为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请及时与本网管理员取得联系,本网将及时予以处理。
鄂ICP备17001920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0598号 建议使用360、火狐、谷歌、IE浏览器以及1024X726像素浏览
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0598号 建议使用360、火狐、谷歌、IE浏览器以及1024X726像素浏览
邮箱:932449293@qq.com whxsmw@126.com 联系电话:18827381718 027-8816 6299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如果您认为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请及时与本网管理员取得联系,本网将及时予以处理。
鄂ICP备17001920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0598号 建议使用360、火狐、谷歌、IE浏览器以及1024X726像素浏览
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0598号 建议使用360、火狐、谷歌、IE浏览器以及1024X726像素浏览